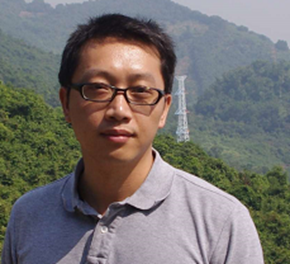90一代青年诗人作品选评论集
黑女 简读90一代青年诗人作品选
楼河 北京诗歌沙龙90一代青年诗人作品选阅读报告
张高峰 语词幻象、美感经验与“众多未来”可能性的生成
——谈“北京诗歌沙龙·90一代青年诗人作品选”
黑女,1970年生人,教育工作者。着有诗集《桃之夭夭》《黑女诗稿》《功课》。曾获第四届
北京文艺网国际诗歌奖一等奖。
简读
一代青年诗人作品选
黑女
在90一代青年诗人眼中,这个世界与我们当年所见的不同,这是自然之事,但当通过他们捕捉的意象和意趣呈现出来时,我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就是文学的生动性。他们观察和体验的角度也更丰富、深刻。
马克吐舟对于指甲的注视是天马行空式的,才气和生气充沛,使整首诗有一种横冲直撞的快感和豪气。
张小榛的《机器娃娃之歌》中,怀胎、螺丝和零件,字符、欢乐和恶徒,孤儿、父亲和先祖,多组关系叠现在一首短诗中,空间感较大,可以塑造出一个时代的景象来。这种写作有前景,有抱负。
王年军的《敲响新世纪的大门》,在虚与实、历史与现实之间穿插,在一种复杂的情感中完成了对上辈人的观察。他诗中“站在人群后面”的父亲形象给我很深的印象,“齿轮”这个词很有力量,表现出他深刻的体验。他这首诗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成熟的。读这些句子,你不必考虑它们的意向和所指,其微妙的戏剧性让诗意朦胧而摇曳。
就女诗人来说,《语文》的戏剧性蕴含的谐谑,背后的东西是尖锐的。《我被摘下心脏》还有一些未被筛查的自我出现在诗中,损害了它的质地。但是我喜欢这些女孩子们诗中体现出的情绪和情感。我从中能看到自己以前的样子。
付炜的《石榴的颜色》,我觉得是勾画出了一代人的精神面目。他对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之思里有许多道暗门,“我知道自己永无可能/做一个全景的人,只能在细节中活着/并惊奇于轮廓的日渐显现”“可我失去了愤怒/失去了所有戏剧性的时刻,仅能轻抚流水/在季节的昏睡里,直抵一枚果核的甜意”。这些句子犀利、清爽,极具现代性。在读第二遍时,我发现由“可”“但”“且”“终”之类连词贯穿起来的“文气”像旋转楼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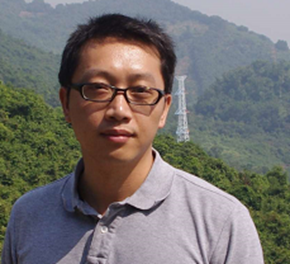
楼河,江西南城人,1979年生。诗人,兼事评论与小说,曾获《诗建设》新锐诗人奖。
北京诗歌沙龙
一代青年诗人作品选
阅读报告
楼河
所谓后生可畏,在谈论年轻诗人的作品时,我们很容易陷入一个常见的负面前提里——年轻诗人缺乏生活经历。从这个负面前提会得出同样负面的结论,比如缺乏真情实感,比如缺乏社会意识,诸如此类。当前辈诗人以这种视角看待年轻诗人时,实际上是用无知掩盖自己的心虚。我不想就这种心理展开谈论,但作为前辈诗人,我认为我们有责任对年轻诗人的认识持开放心态。对于比自己更年轻一代(如果按照现在常说的差三岁就是一代的说法,那是更多代了),我认为仍主要应从共性与差异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写作。尽管一人一首诗的编选方式,既不能体现出某个作者的才能,也无法就此看出代际演变的趋势,但作为一个自以为有丰富写作经验的诗人,我还是在自己的阅读后获得了一点整体上的感受。
在我看来,中国的当代诗(包括文学),也像这个国家的经济与思想一样,处于一种发展的阶段,并没有完全成熟。这个判断意味着,诗歌写作在当前的主要任务可能还是在扩张(或者说探索)边界,而不是寻找(或说守护)核心。假如这个判断是对的,那么从可能性上来说,年轻诗人的未来成就会比现在的前辈们更大,他们会拥有更多的写作资源,更多的训练自身能力的机会。90后诗人与我们(70后)诗人的差异会大于共性。在这些年轻诗人作品里,我们会读到一些与我们当年开始写诗时的那种青涩,那种对社会的不安与梦幻,甚至诗歌主题上的狭窄,但在这些共性之外,其中一些优秀作品所展现出来的自信、成熟更让人惊讶。
后诗人的写作有着更高的起点,这是让我们羡慕的地方,但同时在一种平台化的竞争中也变得越来越内卷,展现了越来越明显的学院化的特征,无论是写作还是阅读,所需要具备的知识储备要求越来越高。本人对这种可能的趋势持保留态度。当写作的能力重要于写作的机遇时,诗歌会越来越退出神秘的地带,逐渐失去我们无法把握的部分。所以在这点上,我会认为生活比阅读重要,它能让我们打破诗歌的封闭化趋势。但这种现象如果是一种负面的后果的话,也不会是90后诗人的责任,它和诗歌在世界中的地位变化有关,也和特殊的外部因素有关。
后诗人的写作展现出了更高的自由度,他们的诗歌技艺多变,诗歌主题也很广泛,这和他们的能力有关,也和他们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化有关。我认为屈从于某种话语体系的压力在他们这里变弱了,诗歌上的政治正确对他们来说没有那么重要,从这点上来说,诗歌可能更加回归了它的本质。
在这两辑作品选里,最年轻的作者是99年出生的,他们这时的年龄和我走进诗坛的年龄相当。回忆自己以及同辈人当年在网络诗歌论坛时期的作品,我确信90后作者比我们那个时代的诗人写得更好。第一辑里,彭杰的《山雀》让我想起史蒂文斯的诗,有一种本体主义的味道,是一首在生活经验中感受超验真实的诗,但写得还不够熟练,可能还没有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语言感觉。但看得出,作者对自己的写作目标抱有很高的期待,因而也写得比较严肃。当我们还很年轻时,实际上是怯于对一些重大主题进行发言的,因为我们会认为自己对于这个世界还不重要,但彭杰有这个勇气,这令人钦佩。可仔的《旷野滑冰场》写得摇曳生姿,对诗歌节奏的营造就显得熟练了许多,但这首诗整体上还是一首倾向于感性的想象力的诗,容得下作者的自由驰骋,需要控制的因素会比《山雀》要少一些。王彻之的《教堂音乐会》在意图上可能和彭杰的《山雀》有相似之处,但显然成熟了许多,不仅控制了其中的理念,还充分展示了诗意,在表达了自我的本真性的同时,还表达了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或某种态度。陈陈相因的《爱人》和赵汗青的《北舞情人》作为爱情诗,都写得生动活泼,但在后者那里,可以读到更明显的性别意识,男性在这首诗里是被欣赏的美的对象,是纯粹的女性角度。第一辑里,李照阳的《海滨来信》可能是最精彩的,句子像风景一样不断呈现,思想也在移步换景中持续生成,绵延、游移、不确定、不可预测,但始终被一种气息控制着。这种气息所透露的诗人与世界的关系是恰如其分的,既没有沉重的负担,也绝不置身事外。
付炜在两辑诗选中都出现了,与第一辑相比,第二辑中的《石榴的颜色》写得太好了,第一辑里的《鸟鸣剧场》还有些套路性的句子。《石榴的颜色》让我有一种读李照阳《海滨来信》的感觉,诗意充沛而绵长。当代诗正变得越来越混融,不再对单一的经验、场景或者事件与观念做出一种总结性的描述,而越来越以展示的方式呈现出一种复杂性。我觉得《石榴的颜色》便具有这种特点。它同时还具有将各种经验综合在一起的特征。而从个人偏好来说,王年军的《敲响新世纪的大门》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诗作,这首情感化的诗歌没有选择以叙事方式来表现,而用知识性的内容使它获得了另一种客观化的角度,“父亲”这个角色在历史和知识的背景下显得更加微茫并具有戏谑色彩,这实际上压缩了情感,并具有了更加普遍化的体验。马克吐舟的《指甲之歌》也是首角度十分新颖的诗,它简直是场华丽舞台上的奇异表演,即使我们不去追问其中的隐喻,句子们夸张而大胆的演出就足够让人激动了。有可能,语言的表演性也是当代诗的一种成果,诗歌未必需要通过语言去追求一种目的性的本质,语言本身就可以成为目的。

张高峰,诗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在读。出版有诗集、研究着作多种。文学评论及诗作散见《文艺报》《新京报》《作家》《名作欣赏》《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理论与创作》《星星》《扬子江诗刊》《诗选刊》《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等期刊。
语词幻象、美感经验与“众多未来”可能性的生成
——谈“北京诗歌沙龙·90一代青年诗人作品选”
张高峰
王国维先生曾言“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随着经济时代与社会情境的剧烈历史变迁,尤其是新世纪后数字媒体、网络传播、云端大数据等影响,加速工业社会生产着无限量的丰富性。人们所置身的生存外在景观世界与日常生活形态的变革,日渐改变着刷新着诗人的内心视像与书写对象,这无疑为新的诗歌写作带来了更新的经验与质素。加之当代汉诗的内部嬗变发展必然,都为新一代的诗歌写作者提供了巨大的诗写资源和可能性,也由此而向人们提出了新的诗写挑战和考验。于此而言90后诗人所体现出的诗歌表达与探求动向,已经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格外关注和试图理解,90一代诗人的诗写崛起,正日渐成为当代汉诗重要而值得深入观察的文学现象。它斑驳而多彩,差异而独特,复杂而包容,在时代急剧变衍和公转加速的眩晕之中,以内心的语言幻象增持着个体自我的精神重力,可以说如何全面而准确地来看待,且有效地理解并进入90后诗人的诗写呈现之中,也向当下诗歌批评界提出了峻切的希冀和渴望,更多的谈谈与讨论90后诗人诗作,可能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话题。
继“北京青年诗会”极力推介80后诗人之后,诗人陈家坪又通过“北京诗歌沙龙“推出90一代青年诗人作品,集中呈现90后诗人诗作的精神气象。他为此曾满怀珍惜和期待地谈到,“一代诗人都会有自己的关键花期,如不能被及时关注,因此被埋没,他们的花期过去,就徒然浪费了,殊为可惜”,他为年轻一代的引介不辞艰辛,殊为不易,令人感动。限于篇幅,“90一代青年诗人作品选”一、二辑入选诗人,每人绝大部分仅编入一首诗篇,集中于短诗,虽然不能完整地传达出每位诗人全面的诗歌丰富性与复杂性,但也向读者部分而集中地呈现出90一代青年诗人独特的诗写语言情态与别样风貌。90后诗人作为一个庞大的诗歌创作群体,同样仍有众多具有独特诗写才能的90后诗人,有待编入后续辑录之中。在“90一代青年诗人作品选”一、二辑中,收入曹僧、王年军、彭杰、罗曼、付炜、可仔、白尔、张晚禾、蒋静米、王彻之、马克吐舟、李照阳、赵汗青、张小榛、陈翔等29位诗人的诗作。其中这一批年轻诗人大部分就读于国内外高校,如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牛津大学、伦敦大学等,从而其诗作中所呈现出的语言技艺、智性转化与知识性气息,都会给人带来某种“学院派”的阅读观感和词语力度冲击,同样这或许也意味着过量语言修辞性的自由度与现实感疏离的悖论。但其极为重要的一方面,也正是90一代青年诗人,在诗歌创作的延续与变革之中,广泛地吸收并激发着语言新的可能性,对于语言的感受性,在这一代人身上正持续发生着微妙而深刻的变化。
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90后诗人在抚触灵魂的方式上与语言的伸展是互为一体的,在他们那里语言的精审与修辞的考究,体现出的是独语与渴望对话的内在张力。在此,语言作为一种迷失般的存在,也往往通向生命凝然冥合的打开,在他们的诗歌之中我们会体会到某种历史生存隐曲的意味。在一个娱乐至死的狂欢化与祛魅化的时代,他们必须经由语言的刷新乃至重置,来实现与持续变动的、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相遇沟通。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通过阅读往往会被90后诗人诗作中,别样而动人的诗写情态所触动,90一代青年诗人已然于语言中寻求着属于自我的形式与精神存在的突围,他们拥有网络与全球化时代丰富的话语资源,也渴望鲜活的生命经验与声音传达,而使得诗写的语境,有了朝向更为开阔的境界而去的可能性。而与此我们的批评视界也许需要不断更新,并为之持续打开,才可以有效地进入到90一代青年诗人的诗歌传达之中,这同样意味着我们的理论透视的地平线,也应与之契合并不断为之后移,才可以与之形成行之有效的言说。
在“90一代青年诗人作品选”第一辑中,彭杰的《山雀》充分地体现出诗人可贵的语言转喻能力,他竭力调动起心象般经验生长的聚合,而使得具象与抽象相凝结,而兼有了语言幻象的穿织之美。这首诗在高密度的意象中完成,保有智性的奇异之感,这同样也使得我们看到彭杰执着于语言本身奥秘的探求,他要在语言分叉的花园曲径里,持谨而自由地伸展创造的活力。可仔的《旷野滑冰场》则于近乎无望的对话祈愿里展开,它是指向诗人内在心灵光焰的,这样的诗性对话,也注定是自我的内心独白和述说,如诗人所写,这样的共舞只能是“在天堂和披满雪被的地下之间,/在弃儿和权势者对垒的斗角场上”,这首诗如同语言的划痕,眷念生命的温度而于亲切的追述中完成,颇富幻想气息。同样其他几位年轻诗人如李照阳《海滨来信》、陈陈相因《爱人》、王彻之《教堂音乐会》、约安《记一个活人的念头》等,都体现出90后诗人彼此可贵的语言自觉与生命省察。
“90一代青年诗人作品选”第二辑中,曹僧的《最最》整饬的诗行之下,难掩自由放恣的语言实验和来自生命内在的怅惘苍凉,同样这是出自于“最”手之笔,它在语言的旋动不息之中,置放难以解开的心愁,化为戏谑调侃的语词,犹如“最刀”,切开耐人寻味的生活意象,“最是一年茫茫尽,你忙迎客,/仓皇而来的最友,手提最酒”。而其中也深蕴着历史生存的暗示性,“最喉舌里有最花瓶,最阶级/看旋转中的最梅,和最世界”。曹僧的诗往往会给人一股勃发的涌动之力,在看似散化的语言流动中实则充满犀利的机锋而饶有深意。王年军是一位有着自我独特诗学思考的诗人,加之他对于影视艺术的研究融入,都深刻地拓宽着诗写的题材领域与省思力度,他的《敲响新世纪的大门》写的颇为精妙,对于语言的分寸感把握的也恰到巧处,由近乎一帧胶片投影般的黑白映像切入,进入场景化的意象之中,“我父亲应该是站在人群后面/当大门摩擦着地面的灰尘/留着仁丹胡的拿破仑/骑马从石砖上经过”,关于历史性的个体反思被隐喻曲折地赋予,显露出一位年轻诗人试图朝向灵魂深处的细腻剖析努力。白尔的《我被摘下心脏》,则于诗尾呈现出惊骇的奇喻语象,“颓败的春天散发出艳丽的死亡气息,/我摘下玉兰花瓣,就像摘掉自己的心脏”,她将一己之情思置于意象的张力扩散之中。付炜的《石榴的颜色》专注于探究喑哑之物的自明,那“时间的对应物”则化为诗人笔下词语的感知,幻象交织联结某种隐微的意识分析,这首诗的美感经验源自思想知觉化的物象穿接,彼此激活。他尝试性地透过诗性分析的界面,而于语言的微妙与含混之中,呈现自我关于存在之物的感知。同样他的《鸟鸣剧场》也显露出独特的语言技艺。侯乃琦《纸星星》、马克吐舟《指甲之歌》、罗曼的《明天更漫长》、杨依菲《返京列车上》、张媛媛《枣子营旧事》、蒋静米《旧教堂》、王奕奕《驰入城镇》等,也都使得我们看到了90后诗人独特而内省的细节性感受与修辞技艺实验。
对于90一代青年诗人的诗作,人们在关注到其语言刷新所形成的诗写可能性的同时,也往往会担心在他们的诗作中,所体现出的语言修辞过剩,由此而来的语言封闭性,是否会阻滞了与现实联系的密切性。这或许是青年诗人语言试炼的学徒期,所必经的一个阶段,正如诗人华清在《毕加索或艺术的辩证法》诗中所写,“要想别人承认你的简单/须由你全部苛刻的繁复,来作为反证”。作为青春期诗歌写作的过渡期,语言形式与结构实验的锻造与探求,成为必经的路径,因为这意味着“技巧往往考验着真诚”。同样作为一种诗性塑形能力的持续成长,90后诗人一代在语言的提升之中,也必然面对着如何力避语言的自我繁殖和实现自我诗写的突破,这可能是诸多诗人必然要面对的困境与难度。从而使得语言技艺成为澄明成为一种更内在而深切的激发,而不至于走入迷失的语言遮蔽当中,从而使得那隐在的诗性“魂线”,真正成为诗写的生命牵引。
诗人王家新曾在《只有真实的手写真实的诗——与青年诗人谈诗》里,引用了《狄欧根尼斯的灯笼——献给曼德尔施塔姆》中诗句,“见习期结束了,你终于明白:/只有以一个瘸子的步态,/才能丈量这坎坷的大地”,这指向了青年诗人在完成了学徒期的技艺试炼后,应有能力向诗写的更深处走去,而使得诗从生命内在的渴望里,获取一股刺痛人心的力量,这同样指向的是在诗的生命内部,始终渴求着一种直抵人心的力量,这样的对于历史生存中生命的触及和摇撼,也只能由“人与世界相遇”的生命给出,而不是其他。诗人忠实于自身命运的召唤,也必定忠实于一颗欢悦而痛苦的历史心灵,在一次诗歌活动后,我曾向王家新老师请教关于诗写提升的问题,仍然清晰记得王老师引用了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话——“终其一生,达成质朴”。这可能也是这位异域伟大诗人历经了一生的总结,语言的生命光泽与笔力的极度准确,也许最终通向的只能是“质朴”,那是凿穿了生存岩层贯通生命体悟的语言形态,它于炽热而冷凝里繁复脱落,袒露生命本真的意境情态。
无论是书写关于生命的欣悦或悲苦,眷念与忧患,诗应然地最终将面对灵魂的担负,作为元诗探求的语言实验,激发词语意象活力与诗性空间的同时,也在喻隐着诗人自我的审美意趣与心灵徘徊。另一方面繁复的修辞技艺,作为一种诗写的能力,朝向的应是深度的意识与无意识领域的精微探察,是面向无垠的生命存在与历史生存的关怀,而须注意力避过度耽溺于语词的能动滑指自我繁殖。诗写必须于修辞技艺的穿透之中,拥有进一步延伸的可能性,最后我想以诗人陈超老师《深入生命、灵魂和历史生存的想象力之光》中的话做结,它仍然对我们当下的诗歌写作有着恒久的启示意义:
未来的先锋诗歌既需要准确,但也需要精敏的想象力;语言的箭矢在触及靶心之后,应有进一步延伸的能力。所谓的诗性,可能就存在于这种想象力的双重延伸之中。
(编辑:夏木)